大学校友访谈栏目杂志阅读、教育学校、简约极简、灰色

2008级文学院校友,文学翻译者,中国翻译协会会员。译有《瑞士的森林》(十周年纪念版)、《千年孤独》(校注本)、《我们七月见》等17部文学作品,其中多部译作被纳入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推荐书目。


曾获"提子翻译出版奖"新人奖,并担任135编辑书展、上海图书博览会特邀译者,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学交流与经典文本的跨文化诠释。


在本次访谈中,他将以译者的独特视角,带我们走进文学翻译的幕后——中国文学在海外面临怎样的真实境遇?AI时代,文学翻译是否仍需要"人"的温度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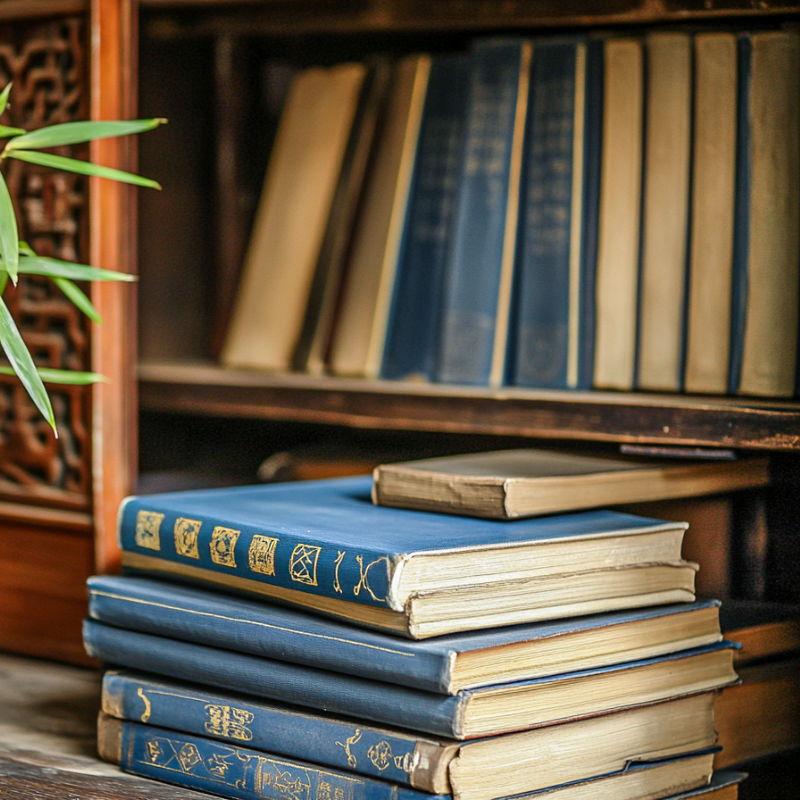
您翻译的克马斯新作《我们七月见》引发热议,有读者称您把"凋谢的玫瑰"译成"褪色的火焰"是过度发挥?

这让我想起博尔赫斯说的"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"。翻译就像带读者参观外国文学的私人书房,既要保持原建筑的骨架,又要让访客感到宾至如归。那个"火焰"的译法,其实是捕捉老克晚期作品中生命灼烧感的尝试。
您看这个句子:"El tiempo no pasaba..."直译是"时间没有流逝",但中文语境里"时光凝滞"更能传递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质感。好的翻译应该像小提琴的琴马——既要牢牢固定,又要让弦自由振动。
这本书的思想是崇尚简朴生活,热爱大自然的风光,内容丰厚,意义深远,语言生动,意境深邃,就像是个智慧的老人,闪现哲理灵光,又有高山流水那样的境界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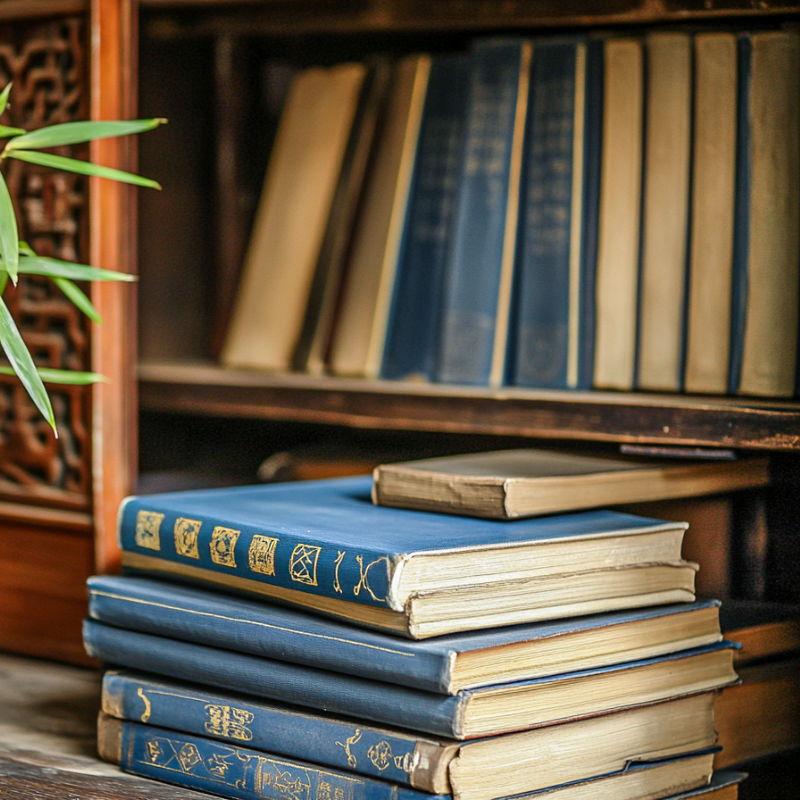
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亲历者,您觉得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存在哪些认知偏差?

去年协助小麦家《人生河河》英文版校译时,美国编辑坚持要把所有谚语加上脚注。但阿拉伯语译本却建议删减景物描写——这很能说明问题。
西方出版社对中国文学有"三件套"期待:乡村叙事、政治隐喻、东方奇观。就像他们总问:"为什么你们不写自己的《百年孤独》?"却忽略了中国作家正在创造的崭新叙事语法。
"当莫言获得诺奖时,我们欢呼中国文学站上世界舞台;当残雪持续落选时,我们才看清这个舞台的台阶有多陡峭。"
建立"语感银行":每天抄写500字经典,培养肌肉记忆 玩"文字俄罗斯方块":把唐诗转换成西语十四行诗结构 经营"副业":我的戏剧社团经历对把握对话节奏帮助巨大

两个小时的访谈里,周笔格手腕上的钢笔始终没放下过。当谈到正在翻译的斯特普鲁时,她忽然望向窗外:"看,这些银杏叶多像正在翻页的书。"或许这就是文学翻译者的宿命——永远站在两种语言的边境线上,把飘落的文字接住,再轻轻放进另一种文化的篮筐。

如果你有机会翻译一本名著
最想挑战哪部作品?为什么?
(精选留言将获赠周笔格亲笔批注的翻译手稿复刻版)

——模版版权说明——
文字 | 来源135AI写作,使用请替换
图片 │ 来源135摄影图(ID:63953、63709)
头图 | 本人原创绘制+135摄影图(ID:63953、18482)
排版 | 135编辑器

